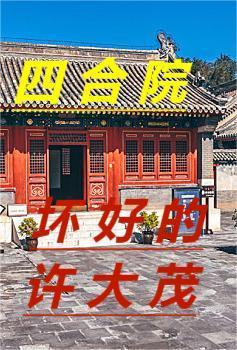九思看書>遲來解藥 > 第4頁(第1頁)
第4頁(第1頁)
他還是那樣的好性子,即便自己有了主意也不吵不鬧,隻是和爺爺在祠堂談了好幾宿。這幾年頂着壓力慢慢做出了點名堂來,家中的質疑和議論才漸漸平息。
“能耐了啊祁冬青,為了個誰也不是的人離家出走!”推測出其中緣由的好友夏澤蘭翻了個逆天白眼,拿指頭狠狠戳他大腿,罵他有毛病,“我還不能說他是罪魁禍首,不然就是給人亂扣帽子,以後被他戳破了沒準得告你诽謗!”
祁冬青這時候總是笑,眉眼裡滿是想起那個人時特有的溫柔和自由帶來的生命力。“不關他事。”他說,“是我自己想的。”
到最後夏澤蘭沒了脾氣,從仁濟出來陪着他瘋,一起守着這家不倫不類的分館。
普通的春日午後,暖融融的風吹來數種花香,竟然有沖淡室内草藥味的勢頭。祁冬青在電腦上确認了一遍下午的安排,原定的兩個預約後面突然多了一個現場号,他仔細看了看,是個名字不熟的老人。
大多數時候新客都認老和春堂的招牌,像這樣誤打誤撞摸到他兒科門診還不掉頭走人的并不常見。祁冬青有點奇怪但也沒細想,哪有拒絕上門客的道理。
先看的兩個小朋友一個外感風寒一個脾虛厭食,都是常見的小毛病。兩個幼崽很乖,看病的時候不哭不鬧,結束了還會甜甜地說句“謝謝醫生哥哥”。
有家長說把握不好火候,問了幾句熬藥的注意事項,忍不住歎道:“沒想到煲藥也不簡單,還得花心思、看功夫。”
“老話常說功多技熟,但誰不盼着一家老小身體健康呀。咱要不得這熟練,您說是吧?”祁冬青一邊寫方一邊回答,“我們也有提供代煎服務,您要是擔心,我這裡給您備注好,晚些去藥房取就行。”
家長連說了幾句謝謝。
為了系統記錄,醫館早就實現了無紙化,藥方都輸在電腦上,但祁冬青過後總會把它們謄抄進簿子裡。這是過去祖輩行醫的習慣,雖然沒有形成規矩,但祁冬青沉浸于筆墨相觸的感覺,長年累月也練就了一手好字。
在等下一個号的間隙,他照例拿起筆,怎料還沒寫幾行,就聽到了的意想之外的聲音。簡簡單單的三個字,深潭般的聲音明明沒什麼溫度,卻燙得他眼眶酸疼。
鐘懷遠。祁冬青不用擡頭,也不敢擡頭,這人出現帶來的震撼如破土而出的新芽,頂穿了血肉,叫他就那樣小小地痛在了原處。
他們曾經說上過一些話,對視過幾秒鐘,林林總總加起來幾幀就能播完,是他藏了那麼多年的全部念想。在感情這事上,祁冬青很蠢很呆,他沒有細數過暗戀鐘懷遠究竟有多少年,糊裡糊塗就把日子這麼過了下去。
畢業之後祁冬青再也沒有見過他,中間家裡能制造很多次機會,但祁冬青不願意在那種生硬的社交場合與他相識,因為鐘懷遠不喜歡。
祁冬青不敢要很多,哪怕隻和鐘懷遠成為普通的朋友,偶爾能說上兩句話也開心。但他也很貪心,不想鐘懷遠和其他人一樣,用奉承調侃的“小少爺”稱呼他,他希望鐘懷遠能夠記住自己的名字。
鐘懷遠教會他走出現狀的勇氣,卻不會教他如何大膽地喜歡一個人。這家分館不僅因鐘懷遠而生根,還處處都是祁冬青拙劣的暗戀技倆和欲蓋彌彰的寄托表達。但凡鐘懷遠留心一些就會發現,診室門口木牌上其實悄悄拼湊着他倆的名字——
“晚風來去吹香遠,蔌蔌冬青幾樹花[1]”。
祁冬青的喜歡藏得深,總是無聲卷起,又在時間中落于微處。他從不否認自己的感情,願意坦蕩地表達出來,卻用着最隐晦的方式。
分館剪彩的那一天,祁冬青在門口的鞭炮鑼鼓聲中,有那麼一刻真的很希望舞獅人摘下頭套來是鐘懷遠的臉。當他今天出現的時候,祁冬青心裡泛起的依然不是苦澀,而是願望成真的開心。
他最希望收到的開張賀禮,一直都是鐘懷遠的現身。
“祁大夫?”或許是祁冬青發呆久了,鐘懷遠又輕輕喚了他一句。
“你認得我?”祁冬青脫口而出,一瞬間的狂喜後立刻覺得不妥,一下放出太遠的眼神光終于聚回面前的桌案,玻璃制的名牌還泛着和他黯然眼色完全不一樣的光。
怎麼會認得呢?過去那麼多可以鼓起勇氣靠近的瞬間,自己都選擇了縮在不遠的暗處裡。祁冬青左手摸到了放在一側的算盤,用珠聲掩蓋自己愈發沒有章法的心跳。
鐘懷遠頓了幾秒,說:“我知道你。”
盡管鐘懷遠換了個概念,讓否認聽起來沒那麼冰冷生硬,但祁冬青依然覺得有些受傷,怎料後面一句才更加傷人——
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,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。
相鄰推薦:七年歡喜+番外 車滿香傳奇 她似甜撩[婚戀] 白糖藍莓 女配在婆媳綜藝爆紅了 八零氣運對照組養崽記 心動謊言 村花她又想作妖了+番外 娛樂圈大清醒 二分之一劇透 來自星星的暗示 白蓮替身,賺爆豪門 頂流營業中 讓我死在你懷裡 神之代号零 清穿之狗皇帝被嫌棄了 團寵小祖宗又在三爺心尖上撩火 逆夏 别想掰彎我 重生後我靠花錢暴富